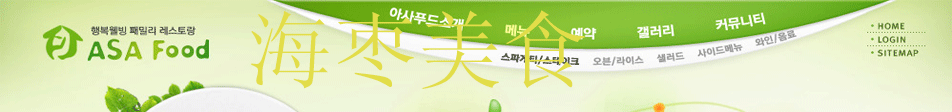|
北京最佳青春痘医院 http://pf.39.net/bdfyy/tslf/210311/8736734.html 十九世纪中期,西学东渐之风吹向日本,大量古代汉籍渐渐被弃置。在此背景下,汉文小说的创作也遭遇了低谷。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,不仅使汉文学受到了巨大冲击,而且改变了其在日本上层社会与文学领域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。 在一味追求西化的激进思潮影响下,汉学成为了腐朽落后的代言词,一度陷入了衰退的窘境。一直到明治二十年左右,人们开始反思对西方文明的过度吸纳,汉学才得到了重新审视并得以再次复兴,逐步开始了明治时期汉文学创作的繁荣期。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,明治汉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式微到复兴的转变。总的来看,可以从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。 “新志”刊物创办与汉文小说刊载 一、官方 维新政令颁布后,明治政府对原本的幕府官学做了改造,并入了以教授西学为主的开成学校和以教授西医为主的医校,重新组建为“大学校”。大学校以“依神典国典,辨国之体,兼而讲明汉籍,以成实学实用。”为办学宗旨,本质上就是追求国学与西学并行。 但对于汉学家和儒学家们而言,这无疑是将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汉学降至了从属地位,因而大学校的建立遭到了学界的剧烈反对。政府宣扬入学是为了追求知识与利益,而非鼓励学习忠孝礼义等德修,可以明显看出汉学受到了压制与针对。官方的表态直接冲击了社会上大量教授汉学的教育机构,原本存于这些私塾、蕃校、家学中的大量汉文典籍与图书渐渐散落流失,取而代之的是西学相关的教材与内容。 但这一政策并未能彻底延续下去,在全面西化的教育方针施行了一段时间后,人们逐渐发现讲究“实学实用”的洋学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汉学的教化作用。为了弥补修正先前过于偏激的政策导致的种种弊端,文部省于年重提汉学的教育作用,并在东京大学开设了“和汉文”专业,四年后又增设了“古典讲习科”。 二、民间 自明治八年以后,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汉学学塾。当时的风气是学生一边在学校修习“洋学”,一边在培养儒学家的学塾中修习汉学。明治时期的文学家有相当一部分都经过了这种学塾的培养,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的熏陶,并接触各类古典汉籍,也自行创作了不少汉文作品。除去这些汉学家,学塾同样培养了许多能够读写汉文,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程度了解的知识分子。 除了国立大学恢复汉学教育、民间开办汉学学塾外,文人间诗会、文会的兴起也促进了明治汉文学的复兴。一方面,这些诗会、文会的成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近代汉文学家,各个团体之间成员交叉重叠,便于彼此交流互动; 另一方面,成员之间往往存在着师承关系,前辈指导后辈、培育新人,形成了良好的文学氛围。加之众多文会成员都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,或与新政府有着联系,也就间接促进了汉学的复兴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明治时期的印刷技术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原本江户时期普及的木版印刷被更为实用的铜板和铅版印刷所取代,书籍的流通随之加速。这种繁荣景象也为当时的汉文作品出版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与途径。东京、大阪、京都等地的报纸种类众多,社会影响力广泛。 不仅报纸,当时出版业的繁荣还直接催生出了一大批汉诗文杂志,在汉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杂志有《新文诗》、《花月新志》、《明治诗文》等。在这些杂志中,有一部分均以“新志”为名,如服部抚松创办的汉诗文杂志《东京新志》,成岛柳北主编的《花月新志》等。这些杂志上刊登的作品都力求贴近生活,追随时代形势,兼具诙谐庄重,涉猎广泛,同时饱含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,很受社会欢迎。 诸多“新志”杂志的办刊初衷不外乎振兴汉学,恢复国学传统,与当时明治政府大力宣扬的西化旗号背道而驰。同时这也为一般民众深入接触汉学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扉,只有根植于群众的文化才能维持长久的生命力,“新志”刊物的创刊者们显然明白了这一点。“新志派”的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了固定群体,在“新志”杂志上连载并获得好评的汉文小说也因为拥有了读者基础,得以更为顺利地出版成册传世。 根据这一批作家的创作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批作家队伍,他们的创作体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变革特征与社会风俗,他们笔下的人物见证、体验了这一时代的巨大变化,这些作品也就具备了记录和见证历史的特别作用。 “新志”小说作家群的形成 面对维新之后全日本翻天覆地的巨变,“新志派”作家们或新奇,或抵触,或欣赏,他们都选择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感受,并将作品发表到了各大杂志上。从文学记录的角度看,这一批“新志”杂志忠实记述了明治时期新思潮冲击下民众生活的变化,以传统汉文作家的笔触来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,极大补充了后人回顾历史的视角;从文学社群的角度看,在这一批作家中,主要以服部抚松、成岛柳北、三木爱花这三人为代表。 一、以服部抚松《东京新志》为中心的作家群 服部诚一,号抚松,出生于福岛县,明治时代的著名文学家、记者。凭借书籍版税,服部诚一得以在东京汤岛置办了豪宅。由于名声盛极一时,有很多人以服部署名自己的作品,或在序文中借用其名。年服部诚一成立九春社,发行了周刊杂志《东京新志》,内容多刊登《繁昌记》风格的汉文和东条竹翠的人情小说等,不乏对名人艳闻和政治新闻的讽刺批评,在当时获得了很大的发行量。 从《东京新繁昌记》到《东京新志》,服部诚一的文体发生了许多转变。从引用六朝作品与六经,到融入净琉璃的文句和汉诗等,将诸多风格融为一体,并开创性地使用自造词,例如将“妾”称为“权妻”,将“官吏”称为“鲶”或“鳅”。 以后者为例,明治初年官场腐败,党派林立,卖官之流屡禁不绝。平民一旦成为官身,立刻蓄起胡须,这也是当时官场的一大现象。百姓对此颇为反感,言语间将大官们的胡须称为“鲶”,将小官们的胡须称为“鳅”或“小鲶”。 在《东京新繁昌记》,《江户繁盛记》之后,又以成岛柳北的《柳桥新志》、石井南桥的《新桥杂记》、菊池三溪的《西京传新记》、总生宽的《东京繁昌新诗》、关槎盆子的《银街小志》等作品较为有代表性。这些作品多描绘其他地方的风俗人情,也属于繁昌记类文体,但销量并未达到服部诚一《东京新繁昌记》当初的盛况。 二、以成岛柳北《花月新志》为中心的作家群 成岛柳北,出身江户。以何有仙史之名创作了《柳桥新志》,创办《花月新志》杂志,以墨上渔史之名创作汉诗文作品,才名广传后世。与其他汉诗文杂志相比,《花月新志》收稿范围广,基本不限制创作题材和内容,汉诗、汉文、和歌以及翻译作品均可刊登。在内容上更倾向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,包括但不限于记录日本社会发展或名流韵事的诗文等。 从《花月新志》选刊的作品可以看出成岛柳北在编辑刊物时的一些个人倾向,他常选用那些贴近现实、引领时代潮流的作品,发表时多青睐能够做到寓教于乐、严肃与诙谐并重的文章。这一方面是为了杂志的发行量考虑,太过于曲高和寡势必使得杂志的受众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;另一方面也寄托了柳北本人的创刊初衷,汉学的壮大需要新血注入,因而创作者与受众间必须达成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,而非汉学家团体内部的互相唱和。 三、以三木爱花《吾妻新志》为中心的作家群 三木爱花,上总(今东京神奈川县)人,本名三木贞一。三木爱花继承了老师服部抚松的办刊理念,从《东京新志》时期就开始磨文笔,积累办刊经验,最终在由自己担任主编的《花月新志》上一一体现。与老师有所不同的是,三木爱花隶属于创新一派的汉学家阵营,他一直在积极尝试新的创作形式,即白话章回体小说,努力为传统汉文小说创作寻找出路。 这一时期也有其他“新志”刊物涌现,如贯名清江创刊的《京华新志》、森川竹溪创刊的《鸥梦新志》等,但主力军还是服部抚松的《东京新志》、成岛柳北的《花月新志》、三木爱花的《吾妻新志》这三本刊物。这三本刊物与其他“新志”刊物一起为当时的诸多汉诗文、汉文小说和其他体裁的汉文作品提供了刊载发行的场所,这一批或创刊或供稿的作家也就集合成了“新志”小说作家群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