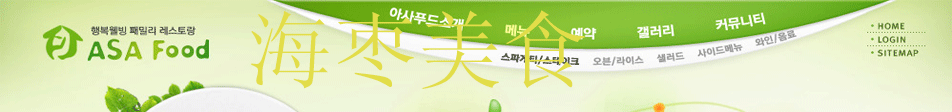|
中科医院曝光资质 https://m-mip.39.net/news/mipso_6010350.html引:如黛中秋节的第二天,约了老邢去白纻山。出城,向南,一路奔向当涂,行到无路处,左拐便是白纻山。一黛横卧,诗书自华。山路从省道拐进小村,一条极是平窄的乡村山路蜿蜒而上。按照导航上的显示,这条山路有五里长。起先我们以为这条山路会到达某个山门,哪知道蜿蜿蜒蜒,我和我的小车就稀里糊涂、懵懵懂懂的开上了山顶!细小的山路久无人迹,除了山岚、虫鸣再无他声,焦黄的松针落满小路两侧,松针间还有许多野栗子、松果散落着,去年的,今年的,寂寞而无人问津。找了一处平缓的地方把车停稳,我和老邢下车走了几步。山顶空气凉爽,山岚轻柔;目之所及,松林繁密,四望无隙。顺着山路再向前走上百来米,山路竟是尽头,密匝匝的松林站在路着,威严肃穆。那些松树都是胸径二十公分左右的次生松林,估计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劳作产物。史籍中传说的七棵古松想来早就做了炉膛劈柴,松涛不再,无旧可怀。相传白纻山上有桓公的挂袍石,我和老邢四目无绪,不知从何寻起。老邢感叹,因为没有一点遗迹,所以一点没有开发。倒是路边一棵小松伸出一段枯枝,黑虬有型,不知可否在不远的将来也有一袭锦袍挂上?实在是找不到一点曾经的文化印记。老邢嘟嘟囔囔的走回车边,取出水壶,于是我们各自喝茶,我的是红茶,他的是绿茶。山风拂面,相对无语。一时间顿生“宁知千载后,荒榛老狐鼠”的感叹。掉头,下山。车子在密密的松针上驶过,平稳而又安静。间或哔哔啪啪的爆裂声,清脆而又干净。我知道,一声“哔啪”就是一粒种子被车轮碾压粉碎,一声“哔啪”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。细小的生命总是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大千世界,如此短暂的轮回,是悲?是欣?是滚滚红尘的梦场?桓公井从山顶下来,经过一段山崖与山坳,松林避让,境界豁然开朗。于是移步山崖,抚松远眺。山崖正对正南,远远望去,薄雾中可以看到远处的姑溪河,波光如练,如白纻之舞,纨袖飞逸,直奔长江。亦有一脉高铁,形若卧龙,交通南北。姑溪河与高铁之间广袤的田畴中,湖渠密布,一个个泛着细密的波纹和光影,仿若“凝睇流盼”的舞女的娇容。崖侧有坳,半亩平缓。走过去,一花衣老妇在整理香烛,烛台南侧,顺阶而下数步,有一水池。我问,这是桓公井么?老妇人操着当地的方言说,是。是就是吧,这样的荒山求证不出什么,不如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。水池圆形,径有三、五米之数,四周无井栏,水面上的井壁为麻石、水泥修葺。井水浑浊,不可见底。老妇人说,是前两天下雨所致。据说,桓公井是当年百姓为桓公连夜所凿,泉水清冽。想来这样的山上凿井不是件易事,恰巧凿到泉眼更是难得。当年的桓公曾在姑孰经营十年,笙歌燕舞不过是桓大司马掩盖野心的招摇。到底,桓温还是个曹操一样的人物,打天下而不夺天下,不愿背上逆臣的恶名,是文人的体统,也是文人的软弱。好在桓公的一切早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,这口井到底还是留了下来。今天的秋意是那样的爽意,纵然是“游山”,一样的“惊梦”嗟叹。不见桓公,空留一井,到底繁华歌笙“都付与断井颓垣”。桓温走了一千六百多年了,可留下了太多的感叹——李白来了,写下了:“桓公名已古,废井曾未竭”;王安石来了,留下了叹息:“歌舞不可求,桓公井空在”。我也在井边踟蹰,很想蹲下身,抄一抔井水。桓公之井清兮,我无我缨濯;桓公之井浊兮,我足岂忍濯?想想,算了,何必矫情,惊扰那些井下的舞魂诗意呢!彼岸花山径两边,林深草密处有很多红色的花朵从地下生出,那是石蒜,我们习惯叫它龙爪花。其实它还有一个阴森森的名字:彼岸花。彼岸花开花的时候,叶子已经腐烂,等花谢的时候,叶子获得新生。佛说:彼岸花,开一千年,落一千年,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,缘注定生死。花与叶永世不相逢的花其实也不少,但是这种彼岸花因为喜欢阴湿之地,又常常在清明开放,留下一些恶名也是前缘。从佛教的角度说,彼岸花又叫曼珠沙华,有天上之花的意思,是天降吉兆的四华之一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,曼珠沙华也是美丽而喜庆的。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,这是佛家教诲人间繁华落尽的懺语,《红楼梦》群芳怡红院夜宴时,曹雪芹用过这个典故。其实这句懺语还有后半句,荼蘼花落,彼岸花在。幽冥之中,黄泉路边,彼岸花静静地开放,引领者魂灵走向彼岸。白纻山寂寥无人,彼岸花开得真诚而美丽。山风拂过,拂动我心底的悲哀,荒草丛中那些彼岸花枝瓣颤巍巍的,临风欲舞。我在想,是不是每一朵花下,都有一个当年桓公殿中的舞娘的舞魂在叹息?当年桓公纵然是郭嘉落帽的风雅,还是长袖纻舞的风流,总也掩饰不了他十年权倾朝野的蛮横与贰心。《晋书》上说他“以雄武专朝,窥觎非望”。桓温自己亦有抚枕狂言:“既不能流芳后世,不足复遗臭万载邪!”可惜,桓温到底是流芳百世,还是遗臭万年却成了一种沉醉的迷离,一方面文学之士把桓温作为风雅名士追捧,一方面正史正统又始终斥其为祸晋篡位的贰臣。功过是非,又有谁人能厘清?林间的风,若隐若无,我仿若看到了醉卧松风的桓大司马,我仿若看到了松林小憩舞袖逶迤的馆娃,我仿若看到了掌灯结伴明妆丽服的舞娘。你看那楚腰曼妙,垂珰散佩,挥一挥手,长袖掩月,皓齿明眸,滴滴香汗落入尘埃。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”,老杜的句子吧。白纻山千年余音松间绕,纵然长袖拂面为君起,总是黄粱!今我来兮,何必叹息?小庙桓公井边,有一些低矮杂乱的建筑。仔细看去,都有供奉,土地庙,龙王殿,观音堂,各有各的名字,却又各自在那些简陋的棚户中安坐。虽然和日常所建庙宇大有不同,甚至简陋中透着些许的滑稽,但是造像庄严,杂乱中自有一番安详与平静。历史上,白纻山上曾有兴国禅寺,想来必然庙堂也兴,香火也旺。今天,白纻山在平静中等待,庙难称堂,僧踪难见,但只要一息香火不绝,就是一颗佛心不灭。夫子曰: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贤人如此,佛更如斯!那位收拾香火的老妇人姓李,应该是位居士,手里拿着半截残香,陪着我两一一介绍。塑料布和铁皮子捆绑的建筑不堪风雨,竹批墙上贴了一张寺庙的规划图,很是壮观,抑或那就是她守望的未来与梦想。大一点的棚子里供奉的是佛祖和观音,地上铺了隔水的塑料布,上面三个蒲团都有频繁跪拜的痕迹。“庙”门旁侧,两支出食台威严肃穆,虽不用供给需要之人,假以时日,也必会普济众飞鸟,传渡一善念。山路,山寺,可以看出当地人对着历史名山的一种遥远的期待。自古名山僧占多,白纻山如果想拂去历史的尘埃,只怕还需借助佛家的力量。想想同属姑孰的凌云山,小九华山,能有今天的规模,都是那些坚毅的僧人,燕子衔泥,锱铢必垒,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。庙成之日,也是修道之时,一日日的坚守,容不得半点偷懒,也容不得半点捷径。这是人生之法,也是修佛之法。历史千载,灭佛的灭法时期也好,兴佛的正法时期也罢,都少不了那些清瘦的和尚,木鱼青灯,守定佛像、佛祖、佛法、佛心,一句佛号一句佛号的修持。是的,在像法的艰难中,再简陋的小庙,都会供养着一颗平静的佛心,风吹不动,雨淋不湿!瓦当绿了顺着李居士指引的路,穿过那几座杂乱的小庙,我向山顶出发。其实,小庙离山顶并不远,目测也就二三十米高,老邢了无兴趣,我只好独自攀爬。好在一条似路非路的泥径,走到头就是山顶。山顶不大,荒草没膝,荆棘扯衣。往东几步是一处山崖,可看东南看过之景;往西,小路漫灭,高墙四围,似有人居,大略是李居士所言的什么庙。我好奇,拨草而行。艰难地绕到墙北,竟然铁门铁将军,不得擅入。索性顺墙再多走几步,高墙之西比邻山崖,树木为之低矮,视野瞬间敞亮。长啸一声,纵览姑孰,全城沉沉于雾霾之中,街衢虽近,细不可辩,再想远望长江,了无可能。当涂诗人郭祥正有过:“隔江望白纻,葱苍压牛渚”的句子,大抵是从和县望白纻山,想想似乎也不大可能,太远太扯了吧?我素来不大喜欢郭祥正,但是他偏偏有一首《中秋登白纻山呈同游苏寺丞》很是应景,引一句吧:“但愿明月照我酒,古来秉烛供遨游”。可惜我来之时,时近中午,山气宁静,月犹在憩。一人独步,金风习习,寂意寥寥,不可久驻,于是狼狈下山。从哪里上来,从哪里下去。到了小庙所在之处,松荫下居然有一小片瓦砾之场。阳光不至,山气润湿,那些断砖乱瓦渐渐的被青苔锈住了记忆,似乎也频添了几分生气与娇羞。 我在瓦砾场转了转,找到两块残片。一片有手掌大小,弧形瓦面,上面刻划着率性的鱼鳞纹;一片仅仅一握,看上去形制古朴,浮雕的芙蓉很是精致,一花一叶,脉络清晰,一张一弛,舒卷优美,是一块很不错的瓦当,可做镇纸之用。 当年的白纻山上,楼台栉比,繁盛一时。“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。这青苔碧瓦堆,俺曾睡过风流觉,把五十年兴亡看饱”!天道循环中,谁知道这块瓦当出自何朝何代?又何须知道呢!尾:远眺离开山路,回到省道,我忍不住停车远眺白纻山。曾经稍显枯黄的山色此时却显得格外的苍翠。历史的余香,婷婷袅袅。我不知道这座沉睡的小山是否还能唤醒昔日的欢颜,我渴望着美丽的舞女,在松林间舞蹈,长袖飘扬,如白色的鸥鹭,浅翔高飞。老邢提议去一趟凌云山,很近,四五公里的样子。于是去了,上了:凌云山的美丽如美颜相机拍摄出的精致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:白纻山还是让它继续地老山荒吧,它无需惊扰。唯如此,我们的记忆才有了几分历史的苍凉。贤三碎碎念~ 长按扫码了解更多内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